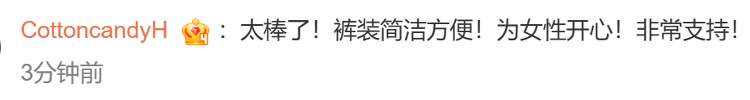神译局是36氪旗下编译团队,关注科技、商业、职场、生活等领域,重点介绍国外的新技术、新观点、新风向。
编者按:他是承担了互联网10%网络请求的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,他的业余项目为一个日后发展成拥有1200名员工以及83000位企业客户的上市企业的诞生创造力灵感,他写的代码奠定了Cloudflare的基石。他还是一位能跟同事和小孩打成一片的亲和人物。但是在公司即将IPO的几年前,他的行为突然变得古怪起来,对项目失去了兴趣,对同事没有了热情,开会再也不能集中精力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经过几年的时间大家才找到了答案。原来是天妒英才,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:额颞叶痴呆症(FTD),一种目前无药可救的病,患者只能慢慢地失去自我,对身边的人毫无感受。SANDRA UPSON聚集了这位天才程序员辉煌又令人遗憾的人生。原文发表在《连线》上,标题是:The Devastating Decline of a Brilliant Young Coder。因篇幅关系,我们分三部分刊出,此为第一部分。
在院子里散步的Lee究竟发生了什么
2019年9月13日,星期五,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互联网安全公司Cloudflare的联合创始人Matthew Prince与Michelle Zatlyn 站在一个狭长的大理石阳台上,俯瞰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地板。Prince周围是公司的高管,已经做好了高呼的准备。Prince敦促大家:“大点声!要大声喊啊!五!四!三!……”上午9时30分,两位公司创始人走过去,敲响了交易所那口著名的大钟,宣告当时的交易拉开大幕以及成立已有10年的公司正式开始上市。这是一次通过仪式,也是他们的发薪日,就在那一刻,很多人摇身一变,成为了百万富翁。
在下面的交易大厅上,过百名员工和投资者也都欢呼起来,他们高高举起手中的手机,捕捉了现场的这一刻。第11号员工Kristin Holloway抬头看着二楼的小阳台,拍了张照片,然后发了条短信转给她的丈夫,公司的第三位联合创始人Lee Holloway。那一刻他正呆在加州的家中。时不时地总有熟悉的面孔穿过拥挤的人群走过来对她说:“Lee应该在这儿。”
在Cloudflare早期的时候, Lee Holloway是公司的常驻天才,他可以闷在电脑前面好几个钟头,一边让指尖倾泻着奔流的代码,一边接受耳机里死亡金属的爆炸。他是建筑大师,正是他的远见卓识,让Cloudflare从画在一张餐巾纸上的草图开始,建设成了一家拥有1200名员工和83000位付费客户的科技巨头。他为这套处理着全球10%的互联网请求,每天阻挡了数十亿网络威胁的系统奠定了基础。他当初设想的很多架构至今依然屹立在那里。
但是在公司准备IPO的前几年,他的行为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。他对自己的项目和同事都失去了兴趣。开会的时候他再也无法集中精力。同事们注意到他变得愈发的死板和好斗,开始拒绝别人的想法,并且无视他们的反馈。
Lee的无礼令老朋友困惑不已。Cloudflare过去就是他生活的中心,他曾经发誓要等到这家初创企业的网络流量超过Yahoo的时候再剪头发。(这个只用了他几个月,或者说长了大概4英寸长的头发。)他一直都是很随和的一个人,总是很乐意指导同事或在午饭的时候到处逛逛。在Zatlyn的生日聚会上,一群小孩被他那写代码的有趣段子给迷住了。没人会认为Lee是个惹事的人。
他的古怪还表现在其他方面。Lee跟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不久就跟一位同事结婚了,这让他的一些同事感到惊讶。他们认为他一定是被巨大的成功和财富冲昏了头脑。Prince说:“我们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赚了一大笔钱,开始另觅新欢。说不定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,打算变成一个混蛋。”
跟Lee走得比较近的人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不管了。他们认为他已经做出了选择,要跟过去说再见了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。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,Lee的性格只会变得更加的乖戾和扭曲,扭曲到就连最了解他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的地步。为什么会这样?找到其中的原因花费了数年的侦探,并迫使他的家人要面对最棘手的人格问题。
在纽交所的那个九月的早上, Lee的弟弟Alaric是在略微有点恐慌的状态下度过的。他跟公司的早期员工合影留念,然后在转发短信给他的哥哥。Alaric从来都没有在Cloudflare工作过,那里的人他几乎都不认识。但是他的黑发就像他哥哥那样独特地掠过前额,他的脸庞就像哥哥一样细长,他的眼睛就像哥哥一样深邃,他的皮肤就像哥哥一样棕黄。Alaric 说:“那真是有点超现实。大家就这么看着我,好像他们都认识我一样。”
跟父母一起呆在圣何塞家中的Lee很是焦躁不安。他就在这幢1550平方英尺的房子的房间和走廊来回走动,两年前从他搬进来以来这里开始这就一直是他的行动路线。他不说话。他的父母打开了电视,当Prince 或者 Zatlyn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,他们就会把他叫过来。
后来,他在家里的Roku前停了下来,开始在在YouTube上搜索Cloudflare的视频。然后他恢复了自己的绕圈:走过走廊,嘴里的腰果嚼得嘎吱作响。
Lee Holloway跟他的小儿子一起在加州中央海岸度过了一段时光
是什么让你成为自己呢?这个问题直指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,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宇宙变得如此特殊的?这个问题的反面又让让我们陷入另一种哲学困境:如果一个人不是他本人,那他是谁?
无数的哲学家已经尝试过要抓住这个难以捉摸的皮纳塔。在17世纪,约翰·洛克(John Locke)把自我和记忆钉在了一起,用回忆作为连接人的过去与现在的线索。这具有一定程度的直观吸引力:毕竟,记忆是我们大多数人表达自我的持续存在的方式。但记忆并不可靠。著名哲学家德里克· 帕菲特(Derek Parfit )在1970年代撰文重塑了洛克的观点,他认为人格来自于更复杂的对跨时间的心理连通性的看法。他认为,许多心理现象(记忆,意图,信仰等)可以形成束缚我们与过去的自我的链条。一个人今天与一天前的很多心理状态是相同的。昨天的你跟前两天的你有着类似的重叠。每一段记忆或者每一种信念,都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延伸的链条,让人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时能够保持住自我。
那么,说某人之所以是他/她“自己”的要义在于,那是因为无数的心理产物能够从第一天保持到第二天,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他的性格慢慢就定型了。相对于灵魂的旧概念,这个定义没那么清晰,不能够提供自我什么时候崩溃的明确门槛。比方说,确定不了人在失去自我之前可以失去多长心理链条(枷锁?)。对于什么造就了你这个问题,神经科学也只能回答一点而已。
神经网络造就了我们的心理产物,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行为的基础。刺激进入大脑,电化学信号嗖嗖嗖地穿过你的神经元,最后激发出一个动作:去拥抱一位朋友。或者坐下来思考。或者抬起头望着阳光微笑。这儿或者那儿损失了一点脑细胞没有什么大不了;神经网络的弹性足以让一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意识保持一致。
但未必总是如此。把脑子里面那团“果冻”糊好以及自我的结构都揭示了它的脆弱性。
Lee的个性几十年始终如一,直到有一天。
他从小就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出庞大的结构。1990年代,Lee在Cupertino出生,他父亲曾在苹果工作过,所以Lee很早就用上了最新款的计算机,是跟弟弟在电子游戏当中长大的。作为游戏玩家的他在朋友当中颇具传奇色彩,因为他能够解读复杂情况,快速调整策略,赢得了无数场游戏。而且他的赢不止于电子游戏。他小时候的好友Justin Powell记得,Lee曾无意间撞见一个中学的象棋俱乐部锦标赛。他不是该俱乐部成员,但最后还是赢得了比赛。但Lee并没有用尖酸刻薄来表现他的聪明才智,从而避免了变得令人厌恶。Powell说:“跟他一起看电影就像看一场《神秘科学剧院3000》。他的存在就在向你发起挑战了,你跟上他。”
Lee和他的朋友会把自己的计算机挪来挪去,到彼此的家里一起玩游戏。他对这种机器本身产生了好奇,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计算机科学,然后又跑到当地的社区大学和圣克鲁斯大学学习,在那里,在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之下他跟Matthew Prince结缘了。
Prince是位年轻的创业者,当时他跑到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去找计算机科学教授Arthur Keller,想实现一个反垃圾邮件软件工具的点子。Keller和他的学生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概念。Prince和Keller以及他的学生同意共享一项专利。而Lee就是这群学生之一,Prince当场就雇用了他。Lee后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经说:“我没想到这个学校项目会变成一个大得多的东西。”
Prince在犹他州的Park City成立了Unspam Technologies。公司驻地距滑雪胜地仅一英里之遥,让他可以纵情地滑雪。Lee搬到了Prince的地下室,一开始是免费打工,食宿全包。但是Lee和Unspam的其他工程师不变的不安分,开始折腾各种业余项目,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做Project Honey Pot的项目,让爬虫一边爬取网络一边跟踪垃圾邮件的发送者。它所做的就是收集并发布垃圾邮件发送者的数据,但并未采取任何阻止措施。尽管如此,这个项目仍然迅速吸引了一篇忠实粉丝。
2007年,Prince离开犹他州去哈佛读商学院,Lee则移居加州,跟女友亚Alexandra Carey住在一起。两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,当时她是Lee所上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的助教。Lee在课上无所事事,还曾经往高架投影仪的透明胶片上乱画笔记来跟教授开玩笑。Alexandra被他逗乐了,不过直到大学毕业后两人的关系才热络起来。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,两人通过一款叫做Savage的多人视频游戏边玩遍聊,维持异地恋。现在,随着Prince离开了犹他州,去找Alexandra自然成了Lee的选择。两人于2008年成婚。
在各自的城市Lee和Prince仍一直继续着Unspam的工作,但是当Prince结束商学院的学习时,Lee打电话告诉他说自己正在考虑其他的工作机会。Prince提出了一个新的相当大胆的建议:他和同学Michelle Zatlyn想到了一个他们认为很有潜力的创业点子。如果他们把Project Honey Pot扩展一下,让它不仅可以识别垃圾邮件发送者和黑客,而且还可以对抗他们如何?其计划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服务器网络,然后说服网站所有者通过这些服务器来对其网络流量进行路由处理,再收集足够的数据来检测其中的恶意请求。这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手段来阻止甚至是全球最大的DoS(拒绝式服务攻击)。但是Prince需要一个技术联合创始人,而这位即将离任的员工就是他的最佳选择。
Prince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小时。在一番高谈阔论结束之后,Lee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。Prince回忆道:“我当时的反应时,‘你还在吗?’然后他说,‘在,看起来能行,我们干吧。’”于是他们就开干了。
他们一起作了个demo,并在2009年底时从两家风投公司那里筹集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。这笔钱足以在Palo Alto的一家美甲沙龙上面租一间经过改建的两居室了,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认真地进行项目的构想。Lee每天都会穿着一样的Calvin Klein牛仔裤,皮夹克,戴上一顶无檐小便帽,然后在一台巨大的ThinkPad笔记本电脑面前埋头苦干,他甚至给那台笔记本起了个名字,叫做Beast。Zatlyn 说:“我们大家有着共同的愿景。Lee是其背后的架构师。他完全被它给迷住了。”
次年,Prince踏上了TechCrunch Disrupt的舞台,在这里,初创企业要为可能拿到巨额融资的机会进行角逐。随着Disrupt的迫近,Prince和Zatlyn 变得紧张起来。Lee已经因为偏头痛而错过了很多天的工作。但距离完成演示似乎还差得很远。大会开始的那天,Prince和Zatlyn忐忑不安地走上舞台,心里祈祷着软件演示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。
Prince开始进行pitch。“我是Matthew Prince,这位是Michelle Zatlyn,Lee Holloway在后面。我们3个是Cloudflare的创始人,”他朗声介绍着,并不时地比划着手势。与此同时,Lee还在后台疯狂地修复了一堆的错误。在运行软件的时候Prince屏住了呼吸,也许是奇迹出现了,软件居然没出问题。它确实有效。就在他登台之后的短短一个小时之内,Cloudflare就吸引了1000名新客户,规模一下子扩大了一倍。
在那次的Disrupt大会上他们拿到了第二名。Prince说:“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,那些我们平时只听说过的神话般的VC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我们。” 在大家的高度关注下,Prince、Holloway以及另一位早期雇员Sri Rao必须不断地给系统打补丁才能维持系统地正常运转。Lee在接受Founderly采访的时候曾提到:“我们9月推出之后在一个月内就接入了10000个网站。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,我们会准备八个数据中心而不是五个。”
译者:boxi。
该文章来源互联网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
- 上一篇: 急,一起帮帮这个七旬老人,救救狗狗们,饥荒中等待救助!
- 下一篇: 我家猫干啥啥不行,睡觉第一名!
相关文章
相关图集
- 出行注意!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
- 积石山地震青海震区30处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部通电
- 住房交易税收新政!购买家庭唯一及第二套住房 不超140㎡按1%缴纳契税
- 三部门:因地制宜将酒店电视终端纳入当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
- 扫一扫免费领礼品?当心“码”上有诈
- 网传河南周口幼儿园一女童遭校车碾轧 当地通报
- 4S店现关停潮,消费者权益谁来保障?
- “预付金”如何变“赋能金”?我国将建立基本医保基金预付金制度
热门推荐
- 网络焦点
- 离奇事件
- UFO
- 社会图库
热门图片
更多阅读
- 古代皇帝为什么临幸嫔妃不能超过半小时?原因是什么
- 问鼎中原的意思和历史背景是什么!
- 陆贞传奇隐藏多位古装美人,萧唤云不及沈嘉敏,第一当之无愧!
- 古代的嫔妃为甚大都无法怀孕?真相是什么
- 为什么嫔妃不能自戕?真相是什么
- 乌拉那拉·如懿为何一生未能如意,成为悲情皇后
- 嫔妃有哪些等级?跟皇后相比有多大差别?
- 这才是清朝嫔妃真正的样子,别被电视剧骗了
- 问鼎中原的典故有何而来?
- 陆贞传奇萧唤云的结局是什么?
- 历史上真实的永世公主,萧唤云与正史形容相差甚远
- 群雄都道问鼎中原,可是谁知道问鼎中原是什么由来呢?
- 虿盆之刑堪称上古酷刑,发明它的人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毒妇!
- 膑刑有多残忍?活活挖下人的膝盖骨,单是想想就觉得疼!
- 热点新闻
- 大话社区
- 图片报道
- 1出行注意!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
- 2积石山地震青海震区30处搬迁集中安置点全部通电
- 3住房交易税收新政!购买家庭唯一及第二套住房 不超140㎡按1%缴纳契税
- 4三部门:因地制宜将酒店电视终端纳入当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
- 5扫一扫免费领礼品?当心“码”上有诈
- 6网传河南周口幼儿园一女童遭校车碾轧 当地通报
- 74S店现关停潮,消费者权益谁来保障?
- 8“预付金”如何变“赋能金”?我国将建立基本医保基金预付金制度
- 9从零破解世界级难题 这个页岩气田首创中国技术体系
- 10住房交易优惠政策12月1日起执行 纳税人如何办理?官方解读
- 11“带头使用国产新能源汽车”,释放哪些“新”信号?
- 121至10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51亿元 同比增长10.9%
- 13“月壤砖”将赴太空!开展太空暴露实验 2025年年底返回地球
- 14多项税收政策调整!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
- 1今上午10点,济南餐饮消费券,开抢了,能减这么多
- 2零点立交转向匝道拆除接近尾声
- 3三角楼打翻 星空调色盘
- 4科技助农 土地托管 一路麦香,这就是丰收的味道!
- 5全国大部气温先升后降 中东部大范围雨雪上线
- 6“假一赔三给4双” 一些电商知假售假为何理直气壮
- 7热门款不发货、退款无渠道……盲盒消费套路深?
- 82021年我国手机上网人数为10.29亿人
- 9欺骗性收费、花式营销,云算命呼唤云监管
- 10广西一女子被多名女子群殴拖行 被三女子按倒暴打拖行
- 11待宰水牛发狂冲进餐馆顶飞男子 该男子被突如其来水牛顶伤
- 12不可思议!天津高速鸵鸟奔跑车辆纷纷避让 车流中飞奔
- 13货车车头冲出悬崖公路悬空 导航走近路,庞大车体进退两难
- 14真的吗?警方通报男子开车撞妻子岳母 一个恍惚错将油门当刹车?